智取AI:李白物我两忘抒苦闷?(组图)
发布 : 2025-11-18 来源 : 明报新闻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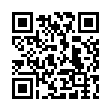
用微信扫描二维码,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
发布 : 2025-11-18 来源 : 明报新闻网
用微信扫描二维码,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

(明报制图)

(明报制图)
一心:最后一句「永结无情游,相期邈云汉」,我参考书中注释,李白明知月亮和影子无情,却仍与它们相约至银河之上共游。书中虽然提到「忘却物我之别,合而为一」等的解释,但我不太明──为何忘却物我之别,就不再寂寞?
文理:不如我们试试问人工智能:
(AI)→ 物我之别:
意思是「外在事物」和「自我」之间的分别。
忘却、合而为一:
指放下区别,不再强调「我」和「外界」是完全分开的,让「我」和「外界」融为一体,从而使心灵自由,不再执著。
杏梅:也就是说,李白打破了物我之间的界限,觉得自己和月亮、影子没有区别,于是「死物」与「人」之间的区别消失了,人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,放下区别,烦恼便不会由此而生。
老师:你们同意这种心态吗?
一心:放下对现实世界的执著,是否在逃避现实?现实是:无论你心灵飞至多远,人总不能脱离当下现实吧!此人是不是缺乏读书人应有的忧国忧民之心?比如杜甫在《登楼》中,便直视现实,痛心国家多难,对国事的关怀溢于言表,这才是我们处世当有的态度!
文理:如此比较有欠公道!《月下独酌》写于安史之乱前,而且李白亦有关怀百姓的一面,他曾写道:「白骨成丘土,苍生竟何罪」,悲痛百姓在安史之乱中遭受的苦难。
杏梅:既然一心想比较李杜二人,我也说一下我的想法──李白真是豪气干云,他曾自比辅佐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的张良[1],自信惊人;又在安禄山攻破洛阳时,自比韩信,觉得自己「有策不敢犯龙鳞,窜身南国避胡尘」,说自己有击退外族的大计,只是无法进呈皇??o?J??被迫南逃。这样读来,同样胸怀大志,杜甫的「日暮聊为梁甫吟」只写自己报国无门,却无李白的自傲。
一心:如此自负之徒,我看他是喝醉了,他不是自称「酒中仙」吗?若是现实之中无从实践理想,就轻言飞上天上,什么「忘却物我之别,追求精神上的自由」,难道国难就会消除吗?这种消极态度不值得学习!
文理:但李白并非没有察觉安禄山之乱的危机,你且读读这首诗:
「君王弃北海,扫地借长鲸……心知不得语,却欲栖蓬瀛。」[2]
他知道唐玄宗任由安禄山坐大,使他位极人臣,如同海中长鲸一般横行无忌。但是,他一个被逐文人,进言又有何用?这是「非不为也,实不能也」。而且,请留意诗中的「却」字。
一心:「却」?
文理:是的,这个「却」字,正说明他对现实的无奈。国难当前,不应避世,但人微言轻,只能走到蓬瀛仙境,成仙遁世──纵使他心知这是不对的。
杏梅:我也想到一首诗。李白晚年身处乱世,唐玄宗逃难退位,唐肃宗自行登基,李白却错投了唐肃宗弟弟永王璘的阵营,获罪下狱并遭流放。他死前所写的《临终歌》,自比大鹏,说孔子已死,无人为他哭泣了。不过我想,就算孔子在生,看见这种徒有大志却无甚作为的人,也不会为他哭吧!如此狂放,若说他能「放下执著」、「物我两忘」,我是万万不敢信的。
一心:唉!李白真是矛盾。
注:[1]《扶风豪士歌》:「张良未逐赤松去,桥边黄石知我心。」
[2]《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》
■阅读理解
根据文章内容,你认为李白能否达到「物我两忘」的境界?
●『参考答案』(表)
■文:胡咏怡 -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毕业,现职中学中文教师。尤好文字之美,亦慕夫子韦编三绝之勤
(本网图文均有版权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至任何印刷品或上载互联网。本网发表的文章若提出批评,旨在指出相关制度、政策或措施存在错误或缺点,目的是促使矫正或消除这些错误或缺点,循合法途径予以改善,绝无意图煽动他人对政府或其他社群产生憎恨、不满或敌意。)
[星笈中文 第178期]
